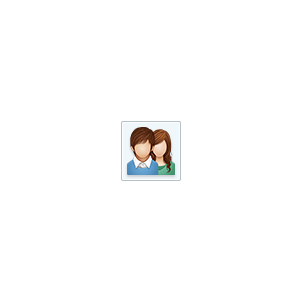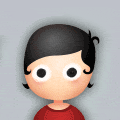隆庆二年三月十六日,送别徐阶后的沈默,悄悄回到了北京城。
在他离京的这三个多月里,京城官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首先是内阁首辅、少傅、建极殿大学士徐阶猝然致仕,原先的次辅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递补为新任首辅。排行第三的太子太保、东阁大学士沈默,自然进为内阁次辅。
然后是六部九卿,左都御史王廷相猝死,由原礼部尚书赵贞吉接任,至于赵贞吉空下的位子,召原礼部尚书、致仕在家的老臣高仪接任。刑部尚书黄光升致仕,位子由南京礼部尚书毛恺接任。
之下还有礼部左侍郎殷士詹转任右都御史督漕运,其职务由吏部右侍郎张四维接任。张四维的职务,由文选司郎中陆光祖接任。大理寺卿杨豫树,升为刑部左侍郎,其职位由原应天府尹孙丕扬接任。詹事府詹事诸大绶任礼部右侍郎……
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官员大换班,才只是初步变动而已,还有更复杂、涉及范围更广的人事变迁,会在之后的日子里慢慢发生。但已经可以从中,看出一些端倪来了:
首先,从表面上看,这是胡宗宪案引起的冲击,内阁首辅、两名九卿大员落马,算是为这起震惊中外的丑闻画上了句号。但从本质看,这却是山西帮和东南帮,针对以徐阶为代表的保守势力,发动的一次成功的抢班夺权。
如果看透了本质,就能理解这一系列变动中的不可思议了:
首先,最不可思议的,就是原次辅李春芳,竟然在蜚声四起的情况下,登上了首相的宝座……这其实是当今朝中三大势力,山西、东南,以及瘦死骆驼比马大的徐党,三派之间博弈的产物。对于这个执掌枢机、宰辅天下的位子,三党都势在必得、又都奈何不了其他两家,只能将和三家关系都不错,又没什么威胁的李春芳留下,使他成为三家的一个缓冲。
其次,才刚回京的吏部右侍郎张四维,竟又升一级,成了礼部左侍郎,明眼人都知道,这是晋党为他下一步入阁在铺路了……对于名声和官声都极佳的子维同学,入阁乃是迟早的事情,就看何时被提上日程了。
还有,新任礼部、刑部二部堂的人选,不是人们之前热议那几位,而是赋闲在家的高仪和南京吏部尚书毛恺,这两位在徐阶跟前极不得宠的老臣。此番老二位能东山再起,跟其背景有极大关系……前者是浙江杭州人,后者是浙江江山人,与当今次辅大人同籍。
当然,这次东南能一举拿下两尚书,也有些运气成分……黄河春汛决堤,淹了黄河半个省,如果堤坝修不好,夏汛的情况将更严重,这时身为工部尚书的朱衡,再去任左都御史,就有些临阵脱逃的意思了。他已经离京去河南督战了,出任总宪之事自然不了了之。
然而都察院乃徐党的喉舌骨干,二百多名御史大半出自徐阶门下,绝对不能看护老巢的位子交给别人。所以赵贞吉只好临危受命,转任左都御史,空出了大宗伯之位……那这个位子,就该身为帝师的殷士瞻担当了。然而殷士瞻贿赂太监、企图入阁的传闻方兴未艾,老殷又是个要脸之人,坚决不接受皇帝的任命,而要求去接手谁都不愿碰的漕务。
他这一举动,是很成功的危机公关,立刻再无人非议于他,皇帝也在其再三恳请下,勉强答应下来。
让来让去,这个位子落在了已经在家赋闲好几年的高仪身上……
除了官场的大震动之外,最近还有一桩夺人眼球的事情,那就是隆庆新朝的首次抡才大典——戊辰科科举的举行。
上月中,便已经举行了会试,两位大主考,乃是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和东阁大学士张居正。这个任命一公布,也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论,但有山西帮鼎力支持,东南也没有异议,那些心中不爽的清流之士,又能如何呢?
不管朝中如何云诡波谲,隆庆朝的第一次春闱,还是得意顺利进行,来自全国的一千六百名举人,经过三天三夜磨成鬼的笔试,又在忐忑不安中等候半个月,已经于月初看到了礼部张贴的皇榜,及第之人自然欣喜若狂,落第的举子则大都如丧考妣,有的直接打点行装,回家继续用功,有的则寄情秦楼楚馆,借那些善解人意的红颜知己,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……不过他们干什么已经不重要,因为人们的注意力,已经全部集中到即将举行的殿试上来。
群众从不关心失败者的命运,这便是现实的无情。
沈默回到家里时,正是殿试的前两天,当天他和家里人一起享一番天伦之乐,聊解没有陪她们过年的歉疚之心。
阿蛮早就在年前到了府上,自然受到了若菡和柔娘的热烈欢迎,对于这个她们当年就无比喜爱的小女孩,两个女人母性大发,对其关怀照料无微不至,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家的长女。而阿蛮的到来,也使沈家略显沉闷的后宅,再次焕发了生机,每日里欢声笑语不断。倒让以为她们会‘望穿秋水’的沈阁老,小小失望了一下。
不过当他看到,梳着靓丽的茴香髻、穿着嫩黄短衣、白绫细腰襦裙,做汉家女儿打扮的阿蛮时,不由一阵错愕。
见他神态反常,若菡对柔娘笑道:“果然,鲜花般的女孩儿,就是比咱们人老珠黄的夺眼球。”
柔娘掩嘴偷笑,阿蛮羞得满脸通红。沈默苦笑道:“就是没见过小阿蛮穿汉装,所以一时没认出来。”
“那,到底是汉装好看呢,还是原来的装束好看?”若菡调笑道。
“都好看,都好看,关键是人好看。”沈默打个哈哈道。
晚上睡觉时,若菡又提起阿蛮道:“一转眼,当年的小丫头,都变成大姑娘了。”
“嗯!”趴在床上,享受着夫人的按摩,沈默闷哼一声道:“是啊!阿吉都成小伙子了。”
对于这个回答,若菡十分满意,手上又加了几分诚意,舒服的沈默快要睡着了。
冷不丁,若菡又道:“我看着,她对你有些意思呢。”
“谁?”沈默的背明显一紧,坐起身来道。
“她呗!”若菡笑眯眯地望着他道:“十六七的大姑娘,该找婆家了。”说着一张粉嫩的俏脸凑到沈默眼前,吐气如兰道:“肥水不流外人田,老爷就把她收了吧!”
“……”沈默的手搭在她滑嫩纤细的腰肢上,眯着眼道:“真不像四个孩子的妈……”
“我跟你说正事儿呢。”若菡正是最火热的年纪,被他的大手轻轻抚摸,便感觉酥了半边娇躯,只是强撑着媚眼如丝道:“老爷就应下吧!省得人家说奴家是妒妇。”说着话,手就搭上了他的小和尚。
沈默苦笑一声道:“我要是应一声,估计就得杖毁人亡了。”
“奴家哪敢呀……”若菡的手心有着丝绸般的触感,小和尚很快便成了大和尚:“不说就算你默认了。”
“我先仗剑斩了你这妖妇再说。”沈默虎吼一声,一个漂亮的鹞子翻身,便将若菡按在床上,肆意轻薄起来。
一番大战到三更。
云收雨歇,若菡慵懒的靠在他怀里,呢喃道:“好狠的人呐,奴家三个月未经人事,你就不能怜惜一些。”
“我不也一样。”沈默舒服的躺着,嘿嘿笑道:“人都说小别胜新婚,又做新娘子的感觉,挺好吧?”
“死样……”若菡紧紧搂住他的脖子,在他耳边呢喃道:“奴家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。”
“我做得还很不够。”沈默谦虚道。
一句话就把好好的气氛破坏了,若菡气得直翻白眼,捏他腋下一把,娇嗔道:“都是当宰相的人了,怎么还这么没正型?”
“那你像个当娘的吗?”沈默嘿嘿笑道。
“……”若菡一时气结,然后夫妻俩笑作一团。
笑完了,若菡正色道:“说正经的,方才跟你提的阿蛮的事,你要好生考虑考虑,我真觉着,把她留下,咱们一起快乐的过日子,也挺好的。”
“这事儿就此打住,”见她再次提起,沈默也只好正色道:“虽然她现在如花似玉、窈窕可人,但在我心里的阿蛮,永远是当年那个奶声奶气、拖着鼻涕的小阿蛮,也许有人有特殊爱好,但我没有!”
“那你干嘛那么看她?”若菡见他不是作伪,便耍赖道:“能不让人往坏处想吗?”
“我是觉着,”沈默无奈道:“她还是穿原来的服装更好看……汉家女人的衣服太拘束,把她的灵魂都困住了。”
若菡听得两眼发直道:“你咋说话老气横秋的呢?”
“我呀!因为我确实老了啊!”沈默闭上眼,叹息一声道:“江湖岁月催人老,所以你也得叫叔叔。”
前半段让若菡心疼不已,后半段却差点没背过气去,夫妻俩便又笑闹起来。待又战了一场,若菡又想起件事道:“你没看着柔娘有些不对劲?”
“没,我眼里只有你。”沈阁老太会说话了。
“死样,白瞎了人家一片痴心。”若菡虽然高兴,嘴上却道:“我知道她是为了什么。”
“什么?”
“又一批平反名单出来了。”若菡轻声道:“还是没有曾大帅的名字,现在先帝时获罪的大臣,还没平反的已经不多了。”
“嗯!”沈默面色郑重起来道:“快了。”
“快了是什么意思?”若菡虽然从来不问政事,但这次得破例了。
“徐阁老在面圣请辞时,向皇帝提出了三个要求,其一就是,希望能给他的恩师夏言平反。”谈到政事,沈默那难得的温柔荡然无存,缓缓道:“现在之所以还没有下文,是因为此事关系甚大,要等我回来再议。”说着淡淡道:“如果夏言平反,那曾大帅自然顺理成章。”
“那太好了,”若菡由衷为柔娘高兴道:“她终于可以一解多年夙愿了。”
沈默却无声叹息,颇感头痛,只是没让若菡看到。
第二天早晨,又与三个小儿女亲昵一阵,到了辰时中,沈默便往前院走去。
到了前书房,却不见二位先生的踪影,警卫告诉他,府上来了许多客人,二位先生在前面招待呢。
“怎么不通报?”沈默微微皱眉道。
“句章先生说,您昨儿才回来,旅途劳顿,就不打扰您了,”警卫道:“只说您什么时候起来,什么时候到前面去就成。”
看来既不是什么重要人物,也不是什么生人,沈默点点头,心里有了数,便往前面走去。
还没到大厅,就听到里面笑声不断,一转过屏风,好家伙,这一屋子人啊!开大会呢。
外间里那些人,虽然在谈天说地,但许多人都留了几分注意在屏风,一见他的身影出现,便叫道:“师相来了……”于是厅里几十号人,纷纷起身向他施礼,一齐道:“学生拜见师相!”
沈默一阵恶寒,竟也有这样叫自己的了。
沈明臣原本笑吟吟地坐在那里,见沈默似乎被眼前的景象闹蒙了。连忙起身道:“大人,这都是您的学生啊!他们听说您回来了,一早就过来拜见,我说您今天可能要歇乏,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起来呢,他们就都在候着,说什么也不肯离去。”
其实听着那一片诚挚响亮的叫声,看着那一张张满是尊敬孺慕的面孔,沈默是一阵阵的心花怒放,脸上写满笑容道:“我的学生还用你介绍?”便亲热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,每个被他叫到名字的,都是心中一暖;尤其那些当年在府学不甚打眼的,听到老师毫不迟疑地把他们的名字叫出,心中那股粗大的暖流,直接把眼眶都顶红了。
王寅和沈明臣看了,除了感动于这份师生情深外,更多的是深深震撼,他们可知道苏州府学有多少学生……足足两千人呐!大人竟然能把在场人都认出来,这是人类所为吗?
其实他们不知道,沈默在南京时,便接见过要应考的举子,事后又批改过他们的卷子,每个人都给与点评。加上他政治家作秀的本能,刻意将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下来,结果现在就用上,为的就是震撼一下这些菜鸟,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所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?沈相公的自留地,也不能长出别人的庄稼。
当走到一个身材壮实,相貌憨厚的学生面前时,沈默轻拍下胸口,一副老天保佑的样子道:“还好你运气不错,没碰到刁难的考官。”这时有脸来看老师的,必是榜上有名者。
众学生闻言都笑起来道:“我们也替他捏把汗,好在他方面阔口,生了个福相。”
原来那学生姓黄,叫金色……黄金色啊!这要是碰上那种喜欢挑刺的考官,能被晃瞎了狗眼,直接打落不取。
黄金色摸着后脑勺,讪讪笑道:“都和家里说好了,这回要是不中,就回去改名……”
“现在好了,不用改了。”沈默大笑着拍拍他的肩膀道:“不错不错!”
一圈走下来,沈默笑的都不会笑了,但到最后一个时,却不由促狭笑道:“你是帮着你叔招待客人呢,还是和他们一起来看我呀?”
被他取笑的那个是沈明臣的侄子沈一贯,也是一副风流机智的样子,闻言讪讪道:“瞧您说的,事不过三,所以四就过了嘛!”
“哦!这么说是过了?”沈默笑着坐回去主座,喝口茶润润嗓子道。
“侥幸,侥幸。”沈一贯嘿嘿笑道。
见有许多人一脸不解,沈默也是说累了,便对沈一贯道:“看来还有不少人,不了解你的丰功伟绩啊!还不给大家讲讲。”
众人便起哄道:“讲讲、讲讲。”
“哎!人都说‘昔日龌龊不足夸’,既然师相有命,学生只好献丑了。”沈一贯收起脸上的嬉笑,道出自己的悲催经历道:“说起来,我是跟师相一年中举的……”此言一出,引得一阵哄笑,众人笑道:“想不到,原来还是个‘老’前辈!”便又是一阵笑。
因为科场成功一靠天分、二靠造化,所以十几岁早达的也有,六十多暮年登第的也有,肯定不能按照年齿论序,而是以及第的早晚为标准……就是说读书人的年龄,是以金榜题名那天为分界线,之前叫虚度,后面才是真正的人生。这样说也有些道理,毕竟读书就是为了及第。
如果你八十了还没及第,可不就等于白活了么?
所以科场论年资与生活中不同,几百年来都是遵循着另一套规矩……除了举人和举人间、进士和进士间,同级比及第时间外;如果对方是进士,而你是举人,那甭管你中举比他早多少年,年纪比他大多少轮,都是人家的晚辈。
所以虽然沈一贯说,自己和沈默是一年的举人,但没有任何冒犯之意,只是自嘲无能罢了。众人也没觉着有任何不妥,只是觉着好笑罢了。
人这一生,肯定会遇到难熬的火焰山,熬不过去,它就是你永远不愿提起的梦魇,可一旦跨越过去,就是你一辈子的骄傲,夸夸其谈的资本。别看沈一贯一贯嘻嘻哈哈!但之前从来不提自己的往事。而现在,就算沈默不提,他也要自己痛说家史:“从嘉靖三十五年第一次赴考算起,我一共考过三场,可每次都名落孙山。第一次文章写得正顺溜呢,却偏偏得了肠痈,疼得我头晕眼花打哆嗦,眼看就要背过气去。我一想,不行,功名事小,生命事大,得先保住命,只能提前交卷,被用篮子吊出去治病。”肠痈就是阑尾炎,能在人生最重要的日子急性阑尾炎发作,沈一贯也不是一般的悲催。
但更悲惨的还在后头,就听他接着道:“接下来三年,我除了读书之外,就是锻炼身体,学了气功、练了铁布衫,心说这下总算百病不侵了吧?再次春闱时,便卷土重来。结果精力旺盛,身强体壮,把文章做得花团锦簇,感觉这次是没问题了。便拿着卷子反复看,摇头晃脑的默读。结果一不小心,在交卷前那天夜里,把桌上油灯碰翻了,卷子弄得跟包油条的纸一样,自然又完蛋了……”
众人方才还笑岔了气,这次却笑不出来了。对于沈一贯的遭遇,他们都感同身受,一点小失误,就会葬送三年光阴,人一生又有几个三年?
“这还没完。”然而沈一贯却很看得开,笑道:“当时悲痛欲绝,好在师相开导我,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……我才挺过那一关。”朝沈默感激的笑笑,接着道:“四十四年那场,我是铆足了劲,自感文章在那一年,算是出类拔萃的了,非要夺取头三名不可的!”他无奈地摇摇头道:“谁知老天爷还没让我苦够,考前一个月,家里来了报丧的,说我母亲大人病故了!没法,只得报了丁忧,回去受制二十七个月。”说到这儿,他深深吸口气,一脸感慨道:“三年一考,我连误三次,十年的光阴就这么白白地糟踏了!要是换了别人,可能早就崩溃了。我也几乎没法恢复过来,”说着他满感情地朝沈默一揖道:“是老师在百忙之中,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,劝慰我、开导我,鼓励我,才让我走出阴影,学会如何面对挫折……”又对众人道:“所以才有了你们看到的,这个整天不知愁的沈不疑。这次要是再取不中,我也不会再伤心难过了,回去该干啥干啥,三年后再来考就是!”
听了沈一贯的话,众人都想到了自己。因为这个年代能从层层科举中杀出重围的。好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岂是那么容易的?不管是世家子弟还是出身贫寒人家,都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,所以他的经历也特别有共鸣。
于是忍不住,又感念起沈默的好,要不是他花费巨资、延请名师,颁布规章、亲自管理,怎能把把苏州府学打造成超越四大书院的当世第一学府?要不是他打破地域之限,允许苏州以外的生员,也可入苏州府学学习,并享受与本地生员同等的待遇,恐怕在座很多人,就没法享受到最优越的教育资源,也没法考出这么多人来了。
还有一点,他们也十分感激沈,只是谁也不会说……那就是去年在南京崇正书院,老师出的那道考较题‘麻冕,礼也’,稍微有些脑子的考生都会明白,身为内阁大学士的老师,在考前出的模拟题,绝对是有指向性的。回去后自然会反复推敲,再联系沈默地批语,也是要求他们尽量保守,心里便会隐约猜到点什么。
在这个一篇制艺定终身的时代,考生对于猜题的狂热和执着,那是不可想象的,既然有了线索,便去按图索骥呗!当时有可能出任主考、又是这种调调的,只有一位,那就是李春芳,当然也不排除老师担当主考,然后出这种调调的题目。
但无论如何,只要把李春芳的旧作习文都吃透,这两种可能就都涵盖进去了。
结果进场一看,主考官果然是李春芳,便把心放在肚子里,按照李春芳的调调行文,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大增。
至少这次在场的诸位,全都研究过李春芳的文章。也成绩也相当不错,会元田一俊,以至罗万化、张位、陈于陛、沈一贯这五经魁中,在场的就有三位……福建田一俊、浙江罗万化和沈一贯。其余诸人也全都在一百五十名之前。
这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十年寒窗的结果,但谁也不能否认,文章符合考官口味的作用。
几乎是自发的,众位新科贡士一起起身,给沈默行大礼致谢。
沈默心里欣慰,嘴上却道:“起来,起来,这是干什么呢?殿试还没举行呢,你们来坐坐也就罢了,可千万别拜我,还是留着拜座师吧!”用闽南话说,他这是典型的‘假仙’。
“一日为师、终生为父,不拜您拜谁?”众人却坚持道:“就是,我们就认您这一个老师。”
“不要乱了官场的规矩。”沈默板下脸来,摆手道:“要是不知好歹,就把你们轰出去。”
“老师言而无信,”这时一个年长些,叫王家屏的学生突兀道。
“哦!这又怎么说?”沈默奇道。他对这个王家屏十分看重。在他看来,此人老陈稳重,有宰辅之器,是个可托付国事之人。
“您当初在崇正书院时许诺过,要在北京给我们接风。”王家屏道:“为了您这句话,咱们苏州府学来的考生,不管中没中,都没有离开北京呢。”
“哎呀!我是说过……”沈默一听,跌足道:“竟然把这事儿忘死了。”其实他根本没忘,而是年前一直处于胡宗宪案的阴影下,根本不合适宴请;年后则去了徽州送葬,昨天才回来,但已然是不合适宴请了……这时候请客,难免会给人抢李春芳买卖的印象,不是沈默平素的风格。
“不瞒老师说我们。”会元田一俊,自然是此刻最有脸的,便笑道:“我们来前,已经包下了整座状元楼,咱们来的这二三十个,只是请您过去赴宴的代表,就算为我们壮行,讨个彩头,也请您破回例吧!”
“是啊老师,您就去吧……”学生们纷纷恳请道。
“盛情难却,”沈明臣也出声道:“别伤了学生们的心。”
连王寅也慢悠悠地道:“去又何妨?”
“好!”沈默终于下定决心道:“同去!同去!”若是以前,他是不大可能答应这种孟浪之举的,然而在天马山上,他悟出了道理,看清了自己的道路。虽然这样做,难免会给人截李春芳胡的感觉。
既然不打算让自己的学生,给任何人当干儿子。沈默便要拿出些霸气来!李春芳不敢怨自己,别人也只是‘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’而已,以他现在的地位,做了就做了,谁还能说什么不成?就算说了,区区几口口水,能奈他若何?
山中无老虎、猴子称大王……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吧!
学生们顿时欢声一片,簇拥着老师便出了府。外面停着个八抬大轿,二话不说,便把沈默推进轿里,也不用轿夫,他们亲自上阵,抬着老师往状元楼去了。
无论如何,这都是桩雅事。
状元楼在京城以高档餐饮著称庙右街,此街从街头到街尾,清一色都是各具特色的高级食府,达官贵人多半在此燕饮饷客,其价位也自然令人高山仰止。
平时在庙右街就算高档的状元楼,在这个大比之时,自然深受想讨彩头、又不差钱的举子们的热捧,一桌席面已经从平时的三两银子,涨到了十两。但你还别嫌贵,自从去年,应试的举子陆续抵京后,这里便日日满座,一桌难求,为了能得偿所愿,举子们竞价出到百两一桌的情况也屡见不鲜。不过包下整座状元楼,这样的大手笔,还是多少年来头一遭!
三层的大酒楼,包一天得多少钱?老板没有透露,但以状元楼的桌数算,早晚开两席,差不多就得六千两。就算有优惠,也不会少于五千两,江浙举子的不差钱,令京城百姓瞠目结舌。
楼上楼下,整整三十多桌丰馔,三百三十多个举子或者贡生,也不是来自一省,有南直的、有浙江的、有福建的、甚至还有江西的,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,都是出自苏州府学,这也是其今日能共聚一堂的原因。
被众星捧月般坐在主位上,沈默笑眯眯地看着楼上楼下,觥筹交错、说笑打诨、串席敬酒,还有提耳罚灌的亲近弟子们。终于体会到了,唐太宗李世民说那句‘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’的豪情与得意。
有道是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。恐当年他还是苏州知府之时,力主教育改革,打破大明官学系统的论资排辈、虚应公事、地域门户、师资薄弱的四大痼疾,加大资金投入、延请名师大儒、对廪生实行考核淘汰、向非苏州籍生员开放入学并一视同仁时,也没想到仅仅过了十年,自己就迎来了累累硕果的收获季节,怎叫人不喜出望外,浮一大白?
不过他也没有得意忘形,知道自己是占了个先发优势,才能把东南菁英荟萃一堂。但他很清楚,这是不可复制的,因为当年全国也只有苏州府学一家,不惜成本、致力于培养优秀应试人才的学院。至于其余省份的官学,不过都是生员们挂名食廪,教授们混口饭吃的地方而已。而那些著名的书院,则深受阳明心血的影响,大都摒弃了对理学的传授,整日清谈无关社稷苍生的玄理空论,或者变成抨击朝政、抒发己见的真谛,就是不治举业。
那些用功读书,渴望以科举进入仕途的莘莘学子,是多么渴望能有一所指点他们学问、帮助他们应试的专门学校啊!
一面是强烈的教育需求,一面是不能提供合格教育的官学、书院,这之间巨大的供求矛盾,使得横空出世的苏州府学,一下子就变成了巨大的磁石,吸引着天南地北的学子负笈而来,拜在他的门下。
当时,东南各省对于本省生员外出游学,是一百个支持的……因为秀才在官学念书是不花钱的,而且官府还得发给口粮,这就是所谓的‘食廪’……洪武二年十月,朱元璋下令在全国各府县建府学、县学,赐学粮,增加师生廪膳。自此,凡入府学县学的学生,一律由国家负担费用,并免生员一家赋税。当时国朝初创,人才匮乏,故太祖高皇帝历年增加廪膳生员名额并给予殊恩优抚。至宣德三年,有感于廪膳生员设置太多太滥,已成各府县之负担,始创定额,一时削减了不少生员数额。此项改革得罪了不少人,只要一有机会,这些人就鼓捣着恢复旧制。
景泰元年,新皇帝登极,为收揽人心,又将生员定额取消。后来成化三年,生员再次定额。正德十年又再次放开生员编制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。许多人削尖脑袋往府学县学里钻,因为一入学校,穿上了宽袖皂边的五色绢布襕衫,就等于跳了龙门。哪怕一辈子考不上举人进士,但只要占着生员名额,照样优免课赋,享受朝廷配给的廪膳。
时至如今,庞大臃肿的生员队伍,已经成为困扰大明财政的‘三冗’之一……另外两个是‘官吏冗员’和‘宗室冗人’。为了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,官府纷纷规定,廪米每月必须本人领取,不得代领,过时不候。对于当时深受抗倭之苦、财政普遍紧张的各级官府来说,本学那些生员们,愿意去苏州游学,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。
沈默却借着苏州开埠带来的巨大收益,以及自己在‘粮食危机’之后,树立的不二威望,强力在苏州推行这项改革,把人家不愿背得包袱自己背,而苏州本地的廪生,只要考核不达标的,却统统开除。这在当时,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,那些被开除的生员骂他,说他‘吃里扒外,不配做本府父母官’,南直的学台也上疏参他,说他‘肆意妄为、破坏祖制’,引来了礼部的申斥。
若非他当时‘六首状元’的光环还未褪去,皇帝和内阁要树立一个读书人的典范,没有追究此事,只是让他稍加收敛的话,恐怕苏州府学的改革,早就半道夭折了。
现在和当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了,随着东南各省重获安宁,海量白银涌入,大户富得流油、官府也变得有钱,在看到苏州府学取代的巨大成功后,自然不再希望本省的学子流失……虽然他们的籍贯仍是本省,但深受苏州教养之恩,感情上会偏哪一边,还真不好说。
虽然沈默的目标,是把苏州府学建成全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,然而他从未有继续垄断下去的想法,因为士子们的学籍都是与户籍绑定,必须回原籍应试。所以如果各省不想继续让学子流失,他们会有无数种办法达到目的,就算是他也没法阻止。
所以去年在南京时,他便主动向那些大家主们提出,希望他们都能大力兴办学校,像培养本族子弟一样,培养本乡本省的人才。虽然当时各大家未必放在心上,但沈默在会试还未举行时有言在先,就不会被认为是闷声发大财的吃独食。
现在,会试的结果肯定已经传遍了东南各省,苏州府学以三百三十人应试,九十七人登第的优异成绩,占据了南榜的三分之二。无论是考中率,还是名次,都远远领先全国。必然会让那些人眼红地跟兔子似的。
其实今日,他之所以不再避讳和这种师生关系,除了要截李春芳的胡之外,还有个重要的目的,就是让那些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家伙知道,门生和座主的关系之上,还有另一种更真挚牢固师生关系!从而下定兴办学校的决心。
正在胡思乱想间,沈默听到学生们叫他,回过神来一看,原来是小二送上一盘冰糖甲鱼。只见那盘中青黄相映,油汁紧裹鱼块,甲鱼头高高的翘着……沈默是过来人,自然认得这道状元楼名菜‘独占鳌头’!
独占鳌头者,状元也。读书人焉能抵御这个彩头的诱惑?但是状元每科只有一个,要是每人一份鳌头,这彩头也就没意思了。所以状元楼的规矩,无论人多人少,只要是一起吃饭的,就只上一只冰糖甲鱼,举子们自会用各种方式,来争抢这个‘鳌头’!
正因为加入了竞争的元素,一心想得这个彩头的举子们,自然会使劲浑身解数,往往精彩纷呈,一些特别精彩的,还会传为佳话,成为状元楼魅力的一部分。所以来这儿的人都知道,每当这盘甲鱼端上来之时,酒席气氛的最高潮也就到了。
按例,应该由席间最尊贵的一位,来决定这个鳌头归谁。当然了,这是个难以抉择的问题,就那一个鳖头,给谁不给谁,都会得罪一大片人,所以最后的结果,就是出题比试,胜者独占!
但这次的情况比较特殊,毕竟还有大半在座的,是没有中第的……这些人就算能想到答案也不会出声,毕竟连贡士都没考上,又有啥脸面抢这个鳌头?
必须要照顾到这些人的感受,最好还得拔拔高,有些教育意义,这才能体现他这个老师的品格……毕竟以利聚,不如以义合,不趁着这些还未入官场的家伙犹有热血的时候灌输,更待何时?
沈默略微一想,脑海中突然蹦出那么一副对联,再一想,也没有更好地了,便无耻道:“我这有个上联,大家可以对一下。”
学生们便全都屏息凝神,楼上的也全都趴到扶栏边,唯恐漏听了一个字。
“这个上联是……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,声声入耳。”沈默说完自己都有些脸红,好在喝了点酒,小脸本就红扑扑的。
‘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……’举子们开始寻思起来,这是个所谓的叠字重字对,但并不复杂,对于爱好此道者,可以说并无难度。然而沈默昔年所对那些绝对,早就成了脍炙人口的传说,在江南广为流传,所以没人以为这位‘对中圣手’是马失前蹄,而是都认为他另有深意。
然而他到底什么意思?这就不好猜了。可不能冷场啊!于是学生们纷纷抛砖引玉……
会元田一俊对的是:‘山色、水色、烟霞色、色色皆空’。
沈一贯对的是:‘松鸣、竹鸣、钟磬鸣、鸣鸣有道’。
此外还有七八个人对了出来,但都不甚欣喜,因为他们自己都觉着,这并不合老师的心意,也不合上联的意境。
这时沈默的同乡门生罗万化,又对出了一个下联道‘家事国事天下事、事事关心’,顿时赢得满堂喝彩,众人都说,正解出来了,不必再对了。
但究竟是不是,还得老师说了算,于是众人都望向沈默,便安静听他缓缓道:“对的都很不错,但是我辈读书人,学的是圣人之学,怀的是济世之心。吟诗作对不过雕虫小技,作一娱乐耳,焉能比出才学高低?”便又话锋一转道:“但我个人最属意一甫所对,风声雨声读书声、声声入耳;国事家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!”说着目光扫过场中众人道:“这也是我对诸位的期许!”
听到老师的话严肃起来,学生们也都收起笑容,聚精会神听他道:“在这里的每个人,都是从小就寒窗苦读至今,经历了数不清的辛苦磨难。这么辛苦读书,又是为了什么呢?”
短暂的安静后,有人轻声道:“金榜题名……”
“我听不见。”沈默淡淡道。
“金榜题名!”学生便大声道。
“那金榜题名又是为了什么?”沈默追问道:“我要听实话。”
大厅里静悄悄的,一时没人回答。
“没有人说,那我替你说。”沈默大声道:“有道是,书中自有黄金屋!书中自有颜如玉!书中自有千钟粟!读书考取了进士,可以光耀门楣、可以出人头地、可以发财致富,还可以去很多房小老婆。对不对?”
众人吃吃偷笑,当然没人敢说是,但肯定有人作此想法。
“如果抱着这样的心思,请你不要再叫我‘老师’!”沈默突然提高声调道:“我沈默不认这样的学生!”
大堂里安静极了,只有他严肃的声音道:“你们应该都知道,如今国事如蜩,四方有难,已经到了不得不的革旧布新,力挽狂澜的地步。此事入仕,必须承担无比艰巨之责任,忍受前所未有之辛苦。如果你想要金钱美女,我劝你去经商,如果你想要舒服安逸的生活,我劝你回家买地当地主,不要指望从官场上得到这些。作我的学生,必须有这份‘先忧而忧、后乐而乐’的觉悟!”说着他举起酒杯道:“如果你还愿意追随我,就干了这一杯!那日后同甘共苦,便是同志!若你不愿追随我,也饮下这一杯,日后若有违法失职、尸位素餐之举,别指望我会念及师生情分!”
“干杯!”学生们一起举杯,饮下杯中的酒水,至于是甜是苦,只有自己知道。